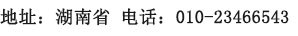“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”,说的是历史上四位有名的皇帝。其中的“汉武”,就是汉武大帝刘彻。正是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,在得知濮阳黄河决口,亲临抗洪一线指挥,最终制服黄河。汉武帝当年在决口处建造的“总指挥部”——宣房宫,至今遗址犹存。
探访遗址
一个初春的早晨,我骑上单车走进新习镇。第一站先来到汉武帝住跸处——洪福寺。洪福寺位于新习镇政府东侧,是一座规模不大的仿古建筑。山门两侧的墙壁上各嵌有两通石门似的古碑,上镌“千”、“秋”、“功”、“延”四个楷书大字,为小庙平添了几分古韵。
入院,一座玲珑的碑亭映入眼帘。亭内为《宣房宫遗址碑》,记载着汉武帝治水造福于民的光辉事迹。院内古木参天,碑碣林立,颇有几分古风古韵。大殿左前方立有一通石碑,上书“武帝行宫犹在,英烈豪气永存”。
洪福寺,为当年汉武帝刘彻瓠子口堵决时的行宫,后周时建寺,宋、明、清重修,后毁于兵燹,“文革”时又遭一劫。寺院西南角,一座门卫房似的“小房子”即“汉武帝庙”,庙内塑有汉武帝像,少了几分霸气,王气,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
离开洪福寺,继续往西南方向骑行不远,下了金堤,过了后寨村,远远地就看到了旷野中的那座小庙以及不远处的大土丘。小庙即著名的“金龙四大王庙”,而那个土丘即是赫赫有名的汉宣房宫遗址。金龙四大王庙前,是一望无际的麦田,也就是当年瓠子河决口处,濮阳八景之一的“龙潭夜雨”。
“龙潭”即黑龙潭。如今这里已经没有水,成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庄稼地。《山海经》称这儿为深渊、繁渊,后来又叫澶渊等,汉代有条瓠子河曾经流经这里。“中华第一龙”在濮阳西水坡出土后,有不少学者考证认为,这里应该是传说中的“雷泽”。《水经注.瓠子水注》云:“成阳、濮阳间有雷泽,舜渔于此”。
66岁的后寨村副支书李家胜说:“要说这宣房宫名气可大啦!中央电视台还来录过像哩!咱脚下的黑龙潭,在年以前还有大片水域,八十年代初,农村兴打压水井,地下水下降了,黑龙潭也就干了。”李家胜接着说:“那时候金龙四大王庙也比现在大,有20多亩,一直到东边奶奶庙那儿都是庙院。这地方是汉朝黄河决口的地方,现在地下两米深还都是大木桩哩。前几年,我领着人打机井,从土堌堆(宣房宫遗址)往这儿一连打了5个眼儿都没打成,底下全是这么粗的大木桩,还有树枝,就这一眼算是打成了”!李家胜指着正在抽水的机井说:“那边桥底下现在还能看到一排木桩哩”!
宣房宫遗址位于金龙四大王庙北米的地方,东侧紧临大广高速。遗址高约7米,长约25米,底部呈不规则的多边形。多年的风吹雨淋,加上附近村民拉土建房,平整土地,如今的宣房宫基址已经看不出当年的模样。
黄河水患
登上土台,眼前视野顿时开阔。深呼吸,一股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。
黄河“善淤、善决、善徙”。自周定王五年(前年)宿胥口(今浚县新镇镇堤壕村附近)决口改道,流经濮阳至今已多年。有记载的决口多达次,改道26次,涉及濮阳境内的就达9次。水患北抵京津,南达江淮。故而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,都把治理黄河当成治国安邦的大事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西汉时期,黄河主河道由滑县东来,沿滑县、浚县、内黄边界进入濮阳境内,在今濮阳新习镇焦二寨、后寨一带打了个弯,折北向清丰、南乐城西入河北、山东境。黄河在新习境内打弯的地方古时叫瓠子,紧靠当时东郡郡治濮阳,是一个重要的渡口和商品集散地。
汉武帝元光二年(年),黄河在瓠子决口,波涛所至,巨野泽被漫。淮河、泗水河道被夺,兖州、徐州、豫州等十六郡成了一片汪洋。灾情上报到都城长安,汉武帝刘彻命濮阳人汲黯、郑当时率领数千囚徒前往堵决,终因水势浩大,堵复不久又被冲毁。
当时武安侯田纷任丞相,他的封地(今山东夏津一带)在瓠子的下游黄河北面,黄河在瓠子向南决口,免除了夏津被淹的威胁,邑中积水可顺利排泄,因而可高枕无忧。而一旦决口被堵,就产生了向北决口的危险,出于私利,上奏汉武帝说:“江河在哪里行走和决口,都是天意,天命不可违。尤其是黄河下游河道,历来游走不定,这种决口非人力能堵,堵塞起来不一定和天意相合。”刘彻是一个很迷信的人,听了这番话不免有些犹豫,就请教方士,这些方士都迎合田纷的说法,汉武帝就信以为真,没再提这件事,一搁置竟达23年,水患也泛滥了23年。
武帝治河
汉武帝元封元年(前年),汉武帝泰山封禅途经濮阳,才发现瓠子决口造成方圆千里的严重灾害。灾区人民流离失所,背井离乡,大大影响了朝廷的赋税收入,于是下决心复堵。
他当即派汲仁、郭昌率五万士卒前往堵决,在将要合龙时,刘彻亲临指挥,看到波涛汹涌的黄河,刘彻仿前世帝王祭水之法,设坛祭祀。并亲自宣读祭词:瓠子决口了,州闾都成了沙,水势一片汪洋,州闾都成了沙啊,大地不得安康。为了堵塞它,山都削成了坑塘。山被削成坑塘也无济于事啊,千年的巨野大泽也被漫溢,鱼鳖滋生,正道废驰,河水湟湟,蛟龙欢唱。天神如不让我封禅巡视,我又怎么知道有这么大的水荒?这水必须回归正道,乞望各位神灵相助,请替我告诉河伯,为什么这样狠心?让我们遭受这么长的祸殃?城邑漂浮,淮、泗横浸,河水这么久不返回正道,哪里还有水的维纲?
祭过之后,又按照当时的迷信惯例,刘彻在堵决处沉入白马、玉壁,祭祀河神。又命随从大将军以下官兵及百姓负薪(背柴草)填土堵塞决口。其法是:于决口水流处,密插楗木,填以柴草,继而负土埴塞。士卒百姓看到皇帝如此尽心尽责,欢声雷动,勇搏激流,一鼓作气将决口堵复。河水被导入北行的两条渠道,恢复了大禹时的情形。黄泛区的人民奔走相告,欢欣鼓舞,从此安居乐业,国泰民安。
汉武帝也非常高兴,当即决定在堵复决口的住处建造一座纪念馆,因皇帝住地原因,就命名为宣防宫。并作《瓠子歌》二首:“瓠子决兮将奈何?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。殚为河兮地不得宁,功无已时兮吾山平。吾山平兮钜野溢,鱼沸郁兮迫冬日。延道驰兮离常流,蛟龙骋兮方远游。归旧川兮神哉沛,不封禅兮安知外。我为河伯兮何不仁?泛滥不止兮愁吾人!啮桑浮兮淮、泗满,久不反兮水维缓……”
司马光抢险
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也随汉武帝参加了这次抗洪抢险,他读了武帝的诗句后,慷慨万端,在其鸿篇巨著《史记》中增辟一篇《河渠书》,记载了这一治黄史上的重要事件。司马迁说:水与人的利害关系太大了,我随皇帝参加了负薪塞宣防决口,为皇帝所作《瓠子》诗感到悲伤,因而写下了《河渠书》。因东郡(濮阳一带)百姓做饭多以柴草为燃料,故征集柴草困难,就征伐淇园(今河南淇县)之竹为楗,渗土堵河成功。东郡长达23年的水患得以扼制。为纪念此事,汉武帝作《瓠子歌》记述堵口之艰辛,并筑宫堤上,名曰“宣房”。
治水如治国,水安则国宁。司马迁把大禹治水与武帝塞河相提并论,盛赞武帝悲悯百姓,并称自大禹以降,开山导水不计其数。然而最为著名的当数瓠子口黄河堵口工程。
瓠子堵决成功,宣房宫名噪一时。历代文人墨客慕名前来凭吊的络绎不绝。东汉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应汤、唐代著名诗人高适、北宋文学家刘岐等,都在此留下了千古诗篇,歌颂汉武帝的功劳。明代濮阳人张弇,在《过宣房宫》一文中,也把宣防宫称为圣地:“寻春来圣地,人道是宣房。波水澄澄绿,馀花冉冉香。良朋频觅句,佳丽共传觞。咫尺潭心在,龙腾振九荒”。
汉武帝虽然死了,黄河也改道了,但人们仍然会怀念汉武帝,仍然颂扬瓠子河堵决治水这一伟大历史壮举。
作者刘平袁冰洁